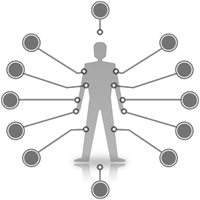“老板,一碗馄饨”,清晨,空气还带着点清冷,不过张大伯的店铺已经恣意地挥洒起了它那充盈的温暖气息。
显而易见,张大伯是个卖馄饨的,按我们这一带的习惯,甭管他姓甚名谁,直接看他的行当叫唤,准没错。如此一来,张大伯的绰号——“卖馄饨的”也就很容易理解了。
但凡制作面点,总少不了和面,醒面,我不知道凌晨四点的洛杉矶长啥样,但凌晨四点的馄饨铺我还是有幸见过几回的。昏黄的白炽灯泡投射下来的光照在白面上,无形中,白面变得像是刚出炉的烤面包一般泛着油黄。
“卖馄饨的”可不管今个儿天气冷不冷,“从家到铺子才多少路啊,六点就该来客人了”。面团被压扁,再被擀面杖擀平,一捻一压,馄饨入锅,捞起,撒上一把葱花,“来喽,馄饨一碗!”。
至少对我来说,每天早上六点吃一碗皮薄馅大的馄饨是那些年里最惬意的事了。
巷尾的馄饨香味是那么的诱人,我倒是以为可以一直吃到这么美味的馄饨。可似乎张大伯没法一直这样做个“卖馄饨的”。
“馄饨不好卖哦”,张大伯擀出一张面皮,手指捻馅,也不见他眼睛有瞟过馄饨一眼,“你看村口那个卖饺子的,人家饺子能卖到一块钱一个,就那个空心萝卜能卖那么贵?不跟你说,去外边等着去。”
是的,“卖馄饨的”手艺确实好,然而这么好的手艺,这么多年都只卖一块五一碗。
“大伯,你就这么卖一辈子馄饨?”我吃着“卖馄饨”的馄饨,操着“买馄饨”的心。
“咋的,不爱吃?”老头儿还真就担心起来了。“不是,我就问问,你咋就没想过涨点价呢?面皮不贵,可肉价蹭蹭地在涨啊!”
“咋没涨价了,涨了好多了,那会儿涨过头了不是,这会儿就缓缓嘛。”张大伯一副“就等着你问”的表情,却是没了后话,留下一脸迷惑的我,欢天喜地地跑去里间了。
这老头真是奇怪。
然后呢,我又是没心没肺地花着一块五,吃着村口十块钱都不见得买得到的美味,一吃又是好多年,“卖馄饨的”的馄饨,始终没涨过价。
再然后,“卖馄饨的”还真就卖了一辈子的馄饨……
张大伯没啥亲戚,来送葬的都是乡里乡亲,丧宴上,每桌上了一大碗馄饨,据说是村口“卖饺子的”包的。本该是竞争对手的“卖饺子的”,那天哭得比谁都伤心,连带着碗里的馄饨貌似都比以往咸。
很多年后,我才从“卖饺子的”口中知道,在很早很早以前,“卖馄饨的”包的馄饨,是不要钱的。
“卖馄饨的”的原型是我老家的一位大伯,写这篇的时候他还健在的,只是借用了他的原型而已。最后一句其实是个开放式结局。不过我最初的设想只是“卖馄饨的”早年接济过村里好多孤儿,“卖饺子的”就是其中之一。